2020年9月24日是曹禺誕辰110周年。作為北京人藝的第一任院長,從1952年建院到生命最后一刻,44年間,他將自己畢生的精力都傾注在劇院的建設與發展上。北京人藝先后上演了他的九部劇作,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原野》《北京人》等作品作為劇院的保留劇目常演不衰,尤其《雷雨》的上演場次更是不計其數。他的作品滋養了一代代北京人藝的導演、演員和舞美工作者,同時促成了北京人藝現實主義演劇風格的形成與發展。
他不止一次這樣說過:“我是愛北京人藝的。因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這個劇院的天地里,翻滾了四十年。我愛那些既有德行又有才能的好演員、好導演和那些多才多藝的可愛的舞臺藝術工作者們。我愛劇院里有各種各樣性格的工人們。我和他們說笑、談天、訴苦惱,也不知道有多少回了。戲演完了,人散了,我甚至愛那空空的舞臺。微弱的燈光照著碩大無比的空洞,使我留戀不舍。”

曹禺
今天就讓我們跟隨著名編劇梁秉堃先生的回憶,重溫曹禺對北京人藝后輩編劇的諄諄教誨。
曾任第一副院長的于是之這樣說:“他會寫戲,又導過戲,演過戲,教過戲,是一位真正懂戲的院長。他是人藝的一把尺子,我們做任何決定都得考慮如果曹禺院長在場的話是否會同意。”
曹禺在劇院里另外一個重要的作用,就是耳提面命地教我們這些年輕人如何寫劇本。
有一次,我請教曹禺:“什么是一個戲的好效果?”
他略微思考了一下回答:“什么叫戲的好效果?是不是演出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,弄得觀眾神情恍惚,全神進入戲境,才算好呢?我以為這不算好的演出。我們始終不贊同把觀眾變成一種失去思索能力的傻子。當然,我們的演出,企圖感動觀眾,使他們得到享受。但更重要的是,我們希望觀眾看了戲后,留有余味,去思考,去懷念。所謂‘含不盡之意,見于言外’,這才是我們朝夕追求的好演出。”
他繼續說,“我們是否完全做到了呢?沒有。有的做到了,有的,遠沒有做到。”我以為,這樣一個戲劇的審美標準是很有針對性的,需要我們深長思之并加以實踐的。
曹禺曾經說過三個“不要寫”:言不由衷的話,不要寫;不熟悉的生活,不要寫;熟悉的生活,但是在沒有從中找出你相信的道理來,并且真正想通了的時候,也不要寫。
我的體會是他在主張劇作家要對待生活真誠,對待創作真誠,對待觀眾真誠,對待自己也要真誠。事實證明,要做到這樣一點是很不容易的。劇作家既需要“識”,更需要“膽”。
在20世紀50年代或60年代的時候,北京人藝漸漸形成了這樣一個慣例——不管是專業劇作家還是業余劇作家,寫戲都要先有一個提綱,而提綱往往首先要請曹禺給“號號脈”。理由很簡單,他的經驗豐富,獨具慧眼,水準很高,能夠一下子判斷出提綱里有沒有“干貨”,值不值得繼續寫下去。
他常說:“一個劇本首先要有‘醬肘子’,光有‘胡椒面’不行!”
然而,請曹禺給提綱“號號脈”,也并非易事。他一貫認為,劇作家的勞動就是想,不斷地想。針對我們“下筆千言萬語,口若懸河無盡”的毛病,便從來不肯聽提綱,而只是看提綱。同時,對提綱的要求也很嚴格,即只能寫在一張有300個字的稿紙上,還要字字入格,多一字不可。這一下我們真作了難,每次寫提綱要使出全身的本事來進行“濃縮”,甚至如同寫詩一樣,字斟句酌,惜墨如金。這時仿佛才體會到,凝練要比鋪陳費力得多。
曹禺看一個提綱,如果不滿意的時候,從來不用激烈的批評詞句,只是輕聲地說“普通普通”“一般一般”或者“現成現成”。為什么會如此呢?因為他一定是發現了你在提綱里,“借用”了別人用過的“套子”。他對于中外古今的經典劇本了如指掌,爛熟于心,在這方面你想蒙混過關是絕對不可能的事。
為此,他提出這樣的觀點:“你要寫一種人物的性格,人物的感情,要構思戲劇的沖突、懸念,你就要了解世界文學作品中已經達到的高度。寫一個守財奴,古今中外都有人寫,莫里哀的阿巴公就達到這類人物性格的高度,你要再寫這種人物性格,就要寫出自己的東西,才能留得下來。一個人的殘忍,有呂后的殘忍,剝皮挖眼,還有各式各樣的殘忍,只有了解了諸如此類人物的性格高度,再寫這種殘忍才不會重復,才會超出已經達到的水平。不熟悉這些,就不會有獨特的創造,沒有這種獨特的創造,是寫不出好作品來的。”
曹禺在創作上從來是另辟蹊徑,不嚼別人嚼過的饃,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,對我們同樣提出如此的高要求,所以寫提綱的時候,不但要注意“短”,更要注意“新”。
一次,我為了把一個劇本的提綱擠進300個字的稿紙里去,整整開了兩個通宵夜車才完成。
當我把提綱給曹禺看的時候,心里總還覺得不滿足,一心想著再補充點兒說明。可是,他擺擺手說:“不用了。一個劇本的提綱寫得越是花哨就越是自欺欺人,或者說,是自欺而又欺不了人。真正有戲的地方,用不了幾個字就能表達出來,因為它們一定會管不住地從你的腦袋里往出跳。我寫《雷雨》的時候,沒有提綱,可是一口氣寫出來第二幕里周樸園、蘩漪和周萍、周沖喝藥的戲,以及第三幕里周萍和四鳳夜半幽會的戲。”

1954年《雷雨》
《雷雨》是曹禺的代表作,也是中國話劇的“代名詞”,演出已有七十多年,在中國家喻戶曉,老少皆知,全世界也已有30多個國家上演,被盛贊為“通俗中的經典,經典中的俗”。
1954年,北京人藝排演《雷雨》,曹禺作為劇作者和院長,在排練前曾多次向導演和演員介紹這個戲的背景材料及創作經過,在排演中,還經常到排練場進行指導,甚至還要動手修改劇本。
這樣一部享有盛名的世界名著,在寫出、演出二十多年以后,劇作家還要修改嗎?是的,進行了修改,而且進行了比較大的修改。這里,僅舉一例。
在第二幕里,蘩漪原來有這樣一大段的獨白:
熱極了,悶極了,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。我希望我今天變成火山口,熱烈烈冒一次,什么都燒得干凈,當時我就再掉在冰川里,凍成死灰,一生只熱熱地燒一次,也就算夠了。我過去的是完了,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。哼!
什么我都預備好了,來吧,恨我的人,來吧,叫我失望的人,叫我嫉妒的人,都來吧,我在等著你們。
沒有想到的是,在這次排練當中,曹禺覺得這段獨白過于冗長了,于是把原有156個字的臺詞,硬是刪改成只有20個字的臺詞——
“熱極了,悶極了,這樣的生活真沒法子過下去了!”
這里,不妨再舉一些例子說明“寫戲切忌平鋪直敘,要反著來”。
這看上去像是很簡單的道理,做起來卻是很難的。為什么?因為這涉及一個戲劇藝術的規律性問題,原則問題。
“反著來”,就是在舞臺上要做一件事又總是遇到阻力而做不成。遇到阻力越豐富,越復雜,越尖銳,越好。于是,就有了很強烈的戲劇沖突,也就是戲。如果“順著來”,只能是平鋪直敘,把復雜多變的生活簡單化、概念化。這是寫戲的一大忌。
“你要先想好了跟誰干再寫。”
寫戲一定要有對立面,而且它必須是強大的,不能一碰就倒;它還必須是復雜的,不是一看就明白;它更必須是多變的,不是始終如一的,恒定的。
“寫戲作不得假,它必須顯露出自己的愛憎來。”
一個劇作者,只有做于我不能不做,止于我不能不止,寫出的戲,才能夠讓觀眾也都愛其所愛,恨其所恨。想想看,劇作者已經把自己的愛和恨全部地、徹底地、生動地奉獻給觀眾了,那么,觀眾怎么還能無動于衷呢?
“要找那些最尖銳的地方下筆。”
“生活中的語言,可不是在用的時候照抄一遍。必須下大力氣加工才成。要把生活中的語言,提高到有個性、有勁道、有高度的概括力量以后,才能用到劇本里去。”
“寫戲如同京劇的武生在舞臺上翻桌子,先翻到三張桌子上去,然后再逼著自己想辦法下來。”
“寫臺詞不能‘一石一鳥’,而應該‘一石多鳥’。也就是說,臺詞既交代了情節,承上啟下,又刻畫了人物,還烘托了氣氛,并且突出了主題思想。”
他在《膽劍篇》中為勾踐寫的長段獨白就是很好的典范:
義士啊,苦成!
你死得其所,你死得比泰山還重。
(走到崖前,望著苦成送來的膽。)
怪不得你送給我這東西——膽哪!
膽哪,你顏色墨而綠,你不美,你不香,你性寒,你苦而澀,一看見你,就知道你的澀是多么難以入口。
你像苦成,苦成又多么像你啊。
你苦啊,膽!可你是清心明目的,你叫我們眼亮耳明,看得見希望,聽得進一切忠言善語。
你苦啊,膽!然而你是退熱的,定身的,使人鎮定,你叫我不焦躁,不慌張。在敵人面前,深思熟慮,知機觀變,要沉靜。
膽,你是多么苦啊。但是你能叫人膽壯,叫人勇敢,敢于面對一切殘暴和不平。
膽,你苦啊。但你是驅毒的,除不潔的。你教我們把一切懶惰、茍安的毛病都一起拋卻,教我們敢于把這骯臟的世界洗得干干凈凈。
膽哪,你不巧言令色,你外面那樣不動人,你心中卻藏了這么多的治國治人的道理!
苦成,這一個膽就頂替了你的千言萬語。這一個膽,就說出了多少死了的壯士百姓深深的心意。
我要天天嘗它,夜夜嘗它,日夜不離它。見了膽,就如同苦成在我身邊。見了膽,就如同見到多少被殺掉的黎民百姓。
見了膽,就會想起“千古的勝負在于理”,而理要多少勞心稍行才爭取到啊。
(衛士對著竹閣,用矛敲了三下,高喊著:“勾踐!你忘了會稽之恥嗎?”)
(沉靜地回答)我沒有忘記。
“讀一個好劇本,在最吸引人的地方,要反復讀。這樣才能讀出‘竅’來。但是,這個‘竅’只在這個劇本里能用,在另一個劇本里就未必能用。所以,抄不得,搬不得。可是,任何‘竅’都有它的‘道理’,如果把這些‘道理’找到了,消化了,那些‘竅門’、招數,才能成為自己的東西。”
我理解,“讀劇本一定要讀透”,什么才是讀透呢?大約,首先是要反復讀,多讀,并且從中琢磨出“竅門”來、“道理”來。其次,把這些消化成自己的東西才能用。
曹禺還說過,“眼高手低”不是貶義詞,而應該是褒義詞。為什么呢?一個人眼高手低才是正常的現象,只有眼界高起來,手下才能跟著高起來。再說,手本來就長在眼的下面。不要怕眼高手低——因為眼高很不容易,要博覽群書,要見多識廣才行,而怕的是眼低手也低。想想看,我們自己不是經常是眼不高,手才低的嗎?
“海是裝不滿的,人的路是走不盡的,感情的長河是流不完的。”
“觀眾是圣人。一個劇作家總要懂得舞臺的限制,我覺得劇作者最大的限制就是觀眾。”
難怪,日本的評論家佐藤一郎作出了這樣的高度評價:“在中國近代戲劇史上,若要推出一位代表作家,當首推曹禺。至少是在話劇界,把他作為近代話劇的確立者和集大成者卻是可能的。曹禺是一個造型力非常卓越的作家,他能大膽地去掉多余部分,其余皆歸我取。他的造型能力使全劇緊緊地把握而成為一個渾然一體的世界,他把滿腔熱情傾注到造型上。這造型能量的源泉來自中國文學的傳統。正是中國傳統內部的造型意識而獲得了近代睿智,這個睿智的名字,就叫曹禺的現實主義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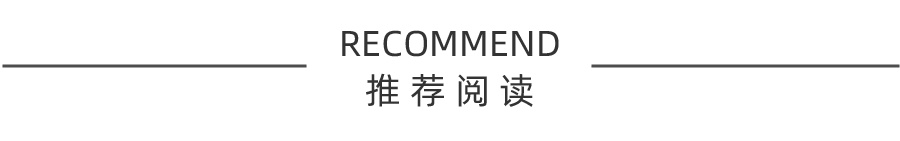

梁秉堃 著
人民出版社青島出版社
《故事中的北京人藝》是國家一級編劇梁秉堃先生所作,講述了他與國家級藝術殿堂——北京人藝半個多世紀的點滴生活,為廣大讀者帶來《茶館》《龍須溝》等經典話劇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。




請輸入驗證碼